5
‘你真幼稚’这句话本来没什么杀伤力。
但这是一个孩子对母亲所说的。
原本毫无攻击力的话因为身份地位的逆转让它的威力在这一瞬间激增。
它像一把锐利无比的尖刀,破开我妈胸膛,刺穿她的皮肉和血管,狠狠地扎在她的心上。
我妈的抓狂来得很是顺理成章。
她刻意忽略真正让她受伤的‘你真幼稚’这句话,而是刻意把矛盾飞速的引向被我打烂的西红柿酱上,以及我对她的态度上。
她认为我再怎么对她不满意也不能糟践粮食。
可下一秒她又会说我凭什么对她不满意,她没少我吃穿,供我念书。
她歇斯底里地崩溃大哭,拍着起起伏伏的胸口说她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
她穿着拖鞋的脚踏在西红柿酱和玻璃碴子上,红着眼睛,指着我的鼻子大骂道:“方思琪!我不欠你的!我们都不欠你的!”
她抓着我衣服撕扯,衣服撕碎的轻声脆响让我烦躁。
她扬起手要打我,抓起地上的西红柿酱要和我‘血拼’。
混杂在里面的碎玻璃割破了她的手,血液和西红柿酱融为一体。
可我拒绝了她的宣战,我抓着她的手腕客客气气把她送出了门。
我没有动手,也没有开腔骂她。
从头到尾,我只是拒绝了她要打我的无理要求。
以前用木头做成的空心门板被她从外面拍得震天响。
她抡起凳子开始砸,带着哭腔的骂声和砸门的咣咣声接连不断、此起彼伏。
不用看,我都知道外面她会是怎样的模样。
像撕开地狱爬出来的恶鬼,张着血盆大口,要把我的骨头和血肉统统撕碎、碾压,拆吃入腹。
小时候她没少对我这样。
那会因为十二岁时办开锁酒席,同学送了我两只小仓鼠。
我妈一向很讨厌带毛的生物。
她说什么都要把小仓鼠扔出去丢进垃圾桶。
我哭着求她,用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来试图和她交易。
我保证我会做一年的家务活,保证我下次考试一定考进年级前五,保证只养这一次……
即使这样的交易并不公平,但我也想留下那两只小仓鼠。
它们的寿命很短,短到只有两三年,短到只能看到两次新年而已。
可我妈不同意,而一旁沉默不语的我爸就是她的帮凶。
或许是我哭闹的声音太大,吵得邻里邻居都探出了头,他们黑黢黢的脑袋扒在窗沿上,好奇地望向里面的我们。
最后是奶奶唉声叹气的劝道:“小孩子的新鲜劲就一阵子,你就让她养几天,无非就是畜生,放在家里也不碍事。”
仓鼠是留下来了。
我要买两个小笼子,我妈不许,她说一个笼子就够了,浪费钱,而且它们还能作伴。
我要买饲料,我妈不许,她说耗子啥都吃,喂点馒头剩饭就能养活。
仓鼠不是老鼠,就连尾巴都一个长一个短,我妈却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我把上网查来的资料摆在她眼前,她连看都不看一眼,说我是放屁,说我在她面前卖弄自己会上网。
仓鼠是独居动物,它们吃专门的谷物饲料。
但是它们饿极了,也会吃掉自己的同胞。
另一只小仓鼠不见了,笼子里只剩下一只。
它的黑眼珠突出得骇人,蓝色的小梯子上残留着一团白色的毛发,混着干涸的血黏在一起。
没多久,它也死了。
它们原本就不长的寿命被我妈缩短到了一个月。
而我妈把小仓鼠的死怪在了我身上,她说是我吵着要养,结果养不好白白养死了。
我在家里大吵大闹,生平第一次掀了桌子,我哭喊着说:“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一个笼子十五块钱,一袋饲料十块钱,买一个会怎样!”
她在厨房切肉,听到我摔东西的声音,想都没想提着菜刀就冲了过来,她说我给脸不要脸,要把我的手指头剁下来。
那天,我妈在骂我,我爸在骂我,偶尔会向着我说话的奶奶也在说我不懂事。
奶奶哄我:“你怎么能因为个畜生和你爸妈没大没小的,死了就死了,以后再买……”
我的哭声破碎,胸口压了一块石头喘不上气。
我哭喊着:“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快十年,我妈依旧会在某天因为一时兴起而重新提起。
她在众人面前戏谑的调侃:“方思琪那会哭着闹着要养耗子,自己养死了反而生我们的气,又摔碗又要离家出走的。”
“是呗,一个耗子没自己爸妈重要,现在的小孩都是这样,都惯坏了。”
……
我妈叫嚣着、不依不饶的脸,和后来的无数个瞬间重合,贯穿了我不长不短的二十年。
6
我和我妈开始冷战,奶奶就像个陀螺一样辗转在我和我妈之间。
倒也难为她八十岁还要操心儿女的事。
她从兜里摸出巧克力糖,像做贼一样塞给我。
她语重心长地说:“你爸还在看守所,判决书现在都没下来,几个月还是几年谁都说不清楚。”
“你妈孤零零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难免脾气炸了些,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你妈啊。”
“她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和你爸拉扯你长大,她无依无靠,能靠的就只有你了,你也该懂事了。”
奶奶的头发已经近乎全白,偶尔几缕灰色掺杂其中,眼皮也耷拉着,瞳孔浑浊,额角那块青褐色的老年斑格外显眼。
看到她年老的模样,辩解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都一把年纪了,土都埋到下巴了,在生死面前,我还有什么资格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何况就算说了,她也理解不了。
后来的几天,我妈开始挨个找人哭爹喊娘,她能一本正经编造荒诞离奇的故事给别人听。
她说,我现在本事大了,管不了了,好不容易求着我回来,我就冲她撒泼发飙。
她说,我把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就差一把火把家里点了。
她还说,我当时刀都举起来架在她脖子上了,恨不得把她杀了泄愤。
我家楼上是自建的麻将馆,我妈就那样每天对着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客人轮流播放她的连续剧。
我妈就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地败坏我的名声。
不过不管他们在背地里怎么说我,当面见了我总会客客气气地和我打招呼。
我妈的麻将馆管晚饭,每天晚上她都会炒一大桌子菜,就连主食都能耐着性子做两样。
她会提前把奶奶和爸爸的那份留出来,而轮到我时,她就会说:“你吃了客人吃什么,嘴巴这么馋?等一会又不是不能吃了,讨吃鬼。”
麻将馆开了多久,我就多久没有准点吃过晚饭,一般客人陆陆续续吃完都九点了。
明明每天的饭都会剩下很多,明明我也可以自己做饭自己吃,明明客人也不介意我一起上桌子吃。
可她从来都不许,我只能吃客人吃剩的剩饭。
她晚上跑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我在看摊,给客人做饭。
她却一直说我不懂事,我不明白懂事这两个字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
直到我妈播放的连续剧到了尾声,她才如愿以偿的出够了气,重新开始和我说话。
她觉得我碍眼,又不肯让我走,她还要我退掉租的房子,彻底搬来家里住。
我没有力气再和她吵架,只说了一句知道了。
我端着炒好的菜上楼,我妈在后面催促着我动作利索点。
几个熟客见了我,开始和我妈说客套话:“思琪都长这么大了,又漂亮了。”
我妈脸上笑着,嘴里却冷哼一声:“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和个妖精一样,学习工作都不上心,倒是在这些事上用心。”
我自始至终都低着头没说话,我妈却又立马改口,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可不能说人家,人家脾气大的很,前几天都差点把家烧了...”
她又打开了话匣子,连续剧又开播了。
我突然觉得那个心理咨询师说的很有道理,逃离原生家庭本就是一个永不能实现的幻想。
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跑出银河系,哪怕是他们死了,他们都会一直在。
他们总会靠着血缘找到我,也总会靠着血缘来打压磋磨我。
血缘已经把我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晚上我妈又跑出潇洒,留下我看摊。
麻将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和灯火通明的光影无疑不是一道热闹的景象。
可此刻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后半夜时,我送最后一桌客人下楼。
走下用锈迹斑斑铁板搭成的楼梯,走过砖墙堆砌的转角,我笑着挥手,和他们说下次再来玩。
一辆黑色的轿车披着夜色而来,一个客人轻车熟路的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车子正要发动时,又突兀地停了下来,车窗一点点降下,里面探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脑袋。
里面的女人披散着头发,盯着我的脸直看,最后问道:“方思琪?”
她突然咧开嘴笑了,她指了指自己说:“是我啊,孟未来,咱俩初中是最好的朋友呀!”
我的脑袋在那一刻停转了几秒钟,细细咀嚼着她的名字。
后知后觉的想起来,我不愿意回忆的初中生涯经历过一场不大不小的校园霸凌。
孟未来就是那场灾难的元凶。
7
她强硬的和我交换了联系方式,并拍着胸脯说自己现在成了心理咨询师,让我有需要来找她。
她想了想又笑着说:“没需要也可以来找我哦,不收费的!”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开朗,笑的时候会露出雪白的牙齿和一点点上牙膛。
要不是她叔叔在催促,恐怕她要抓着我聊七天七夜。
我不会忘了她的样子。
初中时,她笑我的头发是蘑菇头,刘海也很滑稽的剪到了眉毛上三指的位置。
她会在课间时专门坐在我身边和我搭话。
她突然摸了摸我的头,太突然了,突然到我来不及躲开。
下一秒她就捂着嘴大叫道:“小琪!你几天没洗头了呀,你这头发都能炒菜了。”
我妈不让我洗头,她说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就够了,我在学校没人会看我。
孟未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所有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有笑声有嫌弃声。
我敏感又自卑,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只能把头低下,默不作声的看着自己的脚尖发呆。
孟未来一直拍我的背,还弯着腰想看我的脸,她愧疚的问我是不是哭了。
我没理她。
遇到危险时,鸵鸟就会把头埋在沙子里,自我蒙蔽式的躲掉无法面对的难题。
后来,因为孟未来这一嗓子,我在学校算是出了名,大家都知道我不洗头不爱干净。
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解决办法,我妈嫌我洗头浪费水浪费电,还反过来骂我小小年纪不知道学习,就知道臭美。
不爱干净的帽子稳稳扣在了我的脑袋上。
孟未来似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她会挡在我身前努力为我辩白:“不是的不是的,小琪很干净的,真的,她身上香香的...”
得了吧,假好人。
她哭着和我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像是要努力证明自己一样,她抱着我的脑袋使劲的揉搓,嘴里还一直在念:“真的不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我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从我的脑袋上扒下来,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她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想和你交朋友的...”
后来她像是赎罪一般,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开始竭尽所能的接近我,试图讨好我。
我不厌其烦,又不得不妥协,装出一副和她是好朋友的样子。
因为她的人缘很好,我又不想真的被孤立,所以在学校里我能依仗的只有她。
和很讨厌的人做好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大概就是看她怎样都不顺眼,会在心里痛骂她一百遍,最后却笑着和她挽着手一起上厕所。
她买发圈总买双份的,文具也是。
她送我一根亮晶晶的带着廉价玻璃吊坠的自动笔,然后用力地搂着我的肩膀大声宣告:“好闺蜜就要用一样的,闺蜜笔!”
她会扒拉着我的短发要给我扎辫子,她气鼓鼓的说:“小琪留长头发一定很好看,我会买很多发圈,你一个我一个,等到你留长头发,一起用同款。”
她主动和班主任说要和我坐同桌,在班主任面前她一本正经说为了学习,可转过头又冲我嬉皮笑脸:“当然是和小琪一直贴贴啦。”
她放学时不顾我想要回家看摊的请求,死活都要拉着我去逛小吃街。
她笑嘻嘻地说:“你每天都是第一个回家,之前我约你出来你也不出来,就这一次好嘛。”
她买了里脊饼,还加了火腿和鸡排。
她一个我一个。
她蹲在马路牙子上吃的很香,冒着热气又被塞鼓囊囊的里脊饼躺在我手心,烫到手心都麻了。
当天晚上,我就因为放学没有马上回家和晚饭吃得少,而挨了好一顿骂。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形影不离。
初三时,她问我要报哪个学校的志愿,我面不改色的撒了人生中第一个谎。
暑假她还常常来找我玩,我妈见到她时总是很开心。
我妈笑着说:“未来又来找方思琪呀?在里屋呢,死丫头成天不出门,你快拉着她出去转转吧,闷在家里都要长蛆了。”
明明是她不让我出去,因为我出去了,家里的麻将摊就没人看了。
她嘴上这样和孟未来说,可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又会劈头盖脸的责骂我,说我成天野,最好死在外面别回来。
出志愿的那天,凌晨一点多孟未来就给我发来了消息。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喜悦,她说:“小琪!我没日没夜埋头苦读了一年,终于能和你上一个高中了!”
“我去找我爸,让他把咱俩分在一个班,继续做同桌,等你头发再长一点,我就给你编辫子...”
她兴冲冲的幻想着终于等到的未来。
她发这些消息时,肯定是笑着的,一耸一耸的肩膀,雪白的牙齿和微露的牙花子。
可我毫不留情的打断了她,我给她回消息说:“我去了一中。”
然后发送了一张板上钉钉的截图。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才给我打了电话,她努力隐忍着哭腔,故作轻松地说:“小琪,你别开玩笑了,别逗我了,我早就看穿你啦。”
我一字一句的说:“孟未来,我从来都不会开玩笑,绝交吧。”
8
我本来为这一刻准备了长篇大论控诉她的措辞。
可真的到了这一刻,我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料想中大仇得报的畅快没有来,反而是难以言喻的自责和愧疚。
那句‘我讨厌你很久了’的话刚到嘴边,又被我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她的哭声让我烦躁,我挂掉了电话,她就坚持不懈的打来,直到我把她拉黑。
我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洗脑,都是她的错,我没有做错。
后来直到高中开学的前一晚,她都在坚持不懈的每天上门。
我妈就会站在我房间门口,对着我嚷:“方思琪你给我滚出来!你为什么要惹未来不高兴,死丫头真是,我今天就把门砸烂!”
不知道孟未来和我妈说了什么,外面逐渐安静下来。
孟未来离开前,从门缝下塞了一封信。
我看完之后,就撕巴撕巴丢掉了。
我只记得开头和最后一句,她在开头说:“小琪,对不起,我其实知道你很讨厌我...”
她又在结尾说:“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好朋友,以前也是,未来也是。”
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孟未来,因为我高中去了最远的学校,大学也是。
我其实也想过,错的或许不是孟未来,是敏感又自卑的我把原生家庭的恨意加在了她的身上。
我就像一个刺猬,只要有半点风吹草动就会立刻竖起身上的尖刺,无差别的攻击每一个人。
我把社交圈缩到最小,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社交,就这样圈出一块专属我的领地,任何人都不能踏足的地方。
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我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家人,我只想要一个人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悄无声息、不被打扰的活着。
不想有朋友很简单,只需要冷着脸对上他们热切又熟络的目光。
他们找我聊天时,我总是惜字如金,像皇帝批奏折一样,必要时才会回复个‘嗯’。
渐渐的他们就会觉得我很冷漠,冷漠到过于不近人情。
可不想有家人很难。
我必须遵守法律,不能提着刀在家血洒四方。
我也必须要遵守道德,不能对着长辈口出狂言,破口大骂。
我用我的脑袋只想出来逃离这个办法,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却让我坦然的接纳。
自从上次在麻将馆楼下我和孟未来重新加了联系方式后,她就一直给我发消息。
从小猫小狗到和她咨询的病人,包括她早中午饭吃了什么,又或者是她回忆初中,翻出没来及送给我的皮筋和自动铅笔。
从头到尾我都只是在‘嗯’。
说实话,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没有眼力见的人,又或者可以说是神经大条。
不管我如何冷漠的对待她,她依旧坚持不懈要用热脸贴冷屁股,还尝试着要把我这个冷屁股捂得像她的脸一样热。
我妈又一次闯入我的领地,弄乱了我的房间。
那天我也不知道我打扫了几遍屋子,三遍或是五遍,又或者是更多,我只知道手已经被湿布子泡得起了白色的褶。
我翻出手机,打开和孟未来的聊天框,我问她:“强迫症该怎么治?”
她发来一个很可爱的表情包,她说:“小琪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吗?”
在外人眼里,我爸妈一向都对我很好,只是我不领情,成天想要把他们活活气死。
孟未来也是那个外人。
她避开我挑起的强迫症话题,和我聊了很久,发消息不够,她就打电话。
温柔又耐心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比之前那个三百块的心理咨询师靠谱了不少。
她和我聊我爸妈,其实更多的是在聊我妈。
她开始解释,强迫行为的背后其实是焦虑和抑郁。
她总结道:“你知道你妈妈像什么吗?像井底之蛙,而你就是那个一直在和她解释外面世界有多美的小鸟。”
“坐在井底的青蛙,它能看到的只有头顶上一片圆圆的小天空,它当然不相信你说的话。”
“她其实是社会底层的人,孩子就是她仅存的垫底,让她还有一丝尚存的尊严,如果放弃对孩子的俯视,她就又滑落到了底层。”
“她轻贱你、碾压你,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尊严,这就是她发泄痛苦的方式。”
“但你不一样,你是小鸟,你已经扑腾着翅膀飞出了井底,你不需要和她证明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那是她永远都到达不了的地方。”
我也喜欢把我妈比喻成坐在井底的青蛙,我就是那块被我妈踩在脚底、长着湿漉漉苔藓的石头。
但孟未来和我不一样,她把我比作小鸟。
她说我根本不用想如何逃离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已经能飞走了,但是却执着地呆在井边,执着地和我妈证明外面的世界不是她想的那样。
我没得到过爱,所以也不会得到自信。
永远伴随我的是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即使我长出了翅膀,也害怕不能起飞。
最后孟未来轻轻地说:“小琪,你别害怕,你会飞得最高最远,风会托着你,永远都不会掉下来。”
喉咙一阵哽咽,我努力拿出皇帝批阅奏折的架势,从嗓子深处挤出一个‘嗯’字。
我又问道:“孟老师,你一小时很贵吧,我现在可能钱不够,能刷信用卡吗...”
她打断了我,她笑着说:“不要钱的,因为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呀,以前也是,未来也是,小琪。”
9
孟未来没有让我接纳我不堪的原生家庭。
她说小鸟要自由,要飞多远多久,在哪里停留都可以。
我当机立断就收拾好了行李准备滚蛋。
我妈拽着我的行李箱,涨着通红的脸冲我骂道:“方思琪你走,你走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她总是习惯把要死要活的话挂在嘴边。
我从她手里夺过行李箱,我敷衍道:“嗯嗯嗯,到时候再说吧。”
我妈拽下脚上的拖鞋砸在我身上,嘴里谩骂的话像机关枪一样不停歇。
奶奶拦着我妈,她抓着我妈的胳膊,她劝道:“小琪想走就走吧,她长大了,你不能总是困着她,她是个好孩子,她总是要走的。”
我终于离开了这个家。
我退掉了房子,拖着行李奔去了另一个城市,顺便带上了我的猫猫。
我妈用尽了一切能用到的办法逼我回家,搬出奶奶我爸,我只回应她:“哦哦哦。”
她又逼着我爆金币,上礼保险生病买菜,我就说:“我没钱,拿着碗在火车站要饭呢,吃了上顿没下顿,保险上不上的吧,没必要。”
亲戚们受到我妈的号召,轮流发消息轰炸我,让我体谅我妈,让我回家。
我一边啃着板烧鸡腿堡,一边哼着歌把它们挨个删除拉黑,然后退掉了家族群。
我和我妈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她转发痛批子女的小文章,阴阳怪气地在朋友圈嘲讽我,她说她心寒。
我反手给她点了个赞。
我爸的判决书下来,法院打电话给我时,我一个字也不想听,让法院联系我妈。
我成了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仔,每天两点一线的往返公司和小单间。
可不一样的是,我养了很多猫猫和狗狗,还养了鹦鹉和小仓鼠。
家里每天鸡飞狗跳很是热闹,到处都是我妈最讨厌的毛。
可我很开心,这是我想要的生活。
孟未来偶尔出差路过我的城市时,会来看我,她看着一片狼藉的我家感叹道:“小琪,你的强迫症居然治的这么彻底。”
其实我有好好的和她道过歉,为以前的无知和无差别的攻击向她道歉。
但是她却说不重要,她说好朋友也是要吵架的,她不在意。
我这边过得很好,我妈就不一样了。
没几年,她就嚷嚷着自己病了,说自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被划破的口子一直好不了。
我让她去医院,她不去,只知道一个劲地冲我嚷嚷。
她要嚷就嚷,要骂就骂,不去医院就不去,她要怎样是她的自由,我要怎样也是我的自由。
她后来还是去了医院,把检查结果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
她得了糖尿病,发现的时候血糖高得吓人,已经出现并发症了。
她埋怨我不回去,不关心她的死活,不带她去医院。
我有些好笑的问她:“你要不要翻翻聊天记录看看你在说什么,我三番五次让你去医院你不去,你怪我干什么?”
我说的话她从来都不听,倒是别人说的话她愿意听得很。
下一秒我就从她嘴里听到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她的语气无比笃定,她说:“我就是不相信你说的,我就是觉得你不可信,不靠谱。”
她宁愿相信路边买菜大姨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本科毕业,坐在写字楼里工作的我。
在这一刻我突然释然了,小鸟干嘛要管那只坐在井底的青蛙的死活。
没必要。
出于道德伦理的必要关怀,我还是找了一些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和生活起居发给她参考。
她当然半个字都没听进去,反倒是把得病的事情怪在我身上,为了操劳一辈子却换来这样的下场。
我一直没回去过,直到奶奶过世。
我回去之前已经说过,上柱香就走。
奶奶很疼爱我,但我相信她在天之灵能明白,她孙女的委屈和挣扎。
回去的那天,奶奶的遗照被摆在客厅正中央的桌子上。
我规规矩矩的磕头,规规矩矩的上香。
直到要走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我妈。
她哭得泪流满面,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和她打招呼的每一个人。
她着急站起来的时候,腰直接撞上了桌沿,发出一声闷响。
有个亲戚耐心的和其他人解释道:“思琪她妈糖尿病,并发症,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不知道还能看见多少,也是可怜。”
那人听到后,伸出手在我妈面前晃了晃,我妈的眼睛没有反应,却下意识的偏过耳朵。
我的模样这几年变了不少,亲戚们似乎是不太能认得出来,又或者是沉浸在悲痛中,根本不会在意我这个早就离家的不孝子。
或许是母亲和女儿的心灵感应,我刚踏出家门半步,就听见我妈扯着嗓子喊:“方思琪!我知道你在,方思琪,琪琪。”
她毫无征兆的开始崩溃大哭,摸索着挤过人群冲向我,她撞在茶几上,又被马扎绊倒,再被人搀扶起来。
有人劝她:“方思琪那个没良心的早就走啦,她不会回来的,不在这里。”
“是啊,她那种女儿,最好在外面一辈子别回来才好呢。”
我妈摇着头:“不是的不是的...琪琪在这。”
她就那样跌跌撞撞地奔向我。
我小声应了她一句,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
真正的逃离原生家庭从不是在时间和距离上的逃离,原生家庭的阴影会一直在,一直笼罩着每一个困顿挣扎的孩子。
即使他们长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大人,阴影也会一直在。
逃离,是灵魂上的逃离。
奶奶头七的那天,我梦到了她,她和我说她从不怪我,她的孙女受苦了,以后就飞吧。
她会变成温柔的风,轻轻托着我的翅膀,穿过柔软雪白的云,带我飞过高山,飞过小河。
路过青蛙呆着的那口深井时,也不再会停留。
我也不再是孤单一人,那只叽叽喳喳叫孟未来的小鸟也会陪着我一起飞。
飞吧,飞得最高最远,永远都不会掉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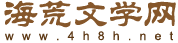
 已完结
已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