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自从父母因车祸去世之后,我更像一片漂泊无依的浮萍。
所以我才会被沈斐玩弄,所以我才会明明好好活着,却签下那份器官捐献协议。
在洗澡的时候,沈斐像蛇一样冲进浴室,坐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而当我满手都是泡沫,他悄无声息地从背后搂住我的腰,在我耳边轻声说:“只要你乖,我不会舍得把你拆开。”
寒意从头漫到了脚。
热水再怎么冒出滚滚白气,我也觉得脊背发凉。
……
换洗过后,我有一种重生的错觉。
沈斐如他承诺,我签下协议之后,他亲自开车送我出了山庄。沈家有钱,房子多不胜数,他不会担心我转头就奔去报警,毕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样的做法很愚蠢。
离学校还有三条街,他停下车。
“自己过去?”他问询我的意见。
我点点头,解开安全带,接过他递来的“诊断书”乖乖下了车。
他喜欢纯白色,喜欢黑长的直发,我按照他的喜好打扮,他自然会看我很久。所以我留下最能掩饰我慌张和欢喜这复杂心情的背影,尽量脚步平缓地往前走。
街口,我咽了口唾沫拐过去。
悄悄回头看,他没有跟过来。
我终于能放下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庆幸我的劫后余生。
只是情绪大起大落,又在黑暗的地方待了那么久,如今车水马龙,人潮拥挤,所有的热闹喧嚣都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的眼眶瞬间酸涩,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世上没有人能帮我,没有人。
将手里那份心理证明拽得很紧,纸张被我捏得脆响,好像快被我的指甲划破。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还要持续多久,却听到一声纤细又温软的声音:“姐姐别哭啦!”
抬头,我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正目不转睛地看我。
她穿着邻街那所中学的校服,皮肤白白的,眼睛大而清澈,最多初一初二的模样。
她手上拿着一张方方正正的纸巾,很香,是熟悉的味道。
初中的时候我最喜欢用这个牌子的纸巾,怔怔盯着她的手,我仿佛被她扯回了我的曾经。
初一那年,我十二岁。
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老师……
我原以为我会在这里学到很多知识,但后来我才发现,我学的远比知识要多得多。
那时无论男生女生都喜欢抱团,不抱在一起的,就会被远远排挤在外。而像我这样胆小、孤僻、自卑的女生,永远都是被他们欺负的对象。
所以我会在体育课后,看到我的水杯里被人恶意吐了口痰;会在作业传下来的时候,被前面的同学撕破两页;会在拿到第一名奖状之后,发现上面留下了黢黑丑陋的脚印……
那些恶意将原本就神经纤细敏感的我逼疯。
又是一次毫不留情地羞辱,我紧紧捏住班长当着全班同学朗读过的日记本,站到了楼顶上。
意识恍惚,天空却湛蓝。
我沉浸在那片纯粹的蓝色中时,是赶来的沈斐救了我一命。
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很感谢他。
直到我发现那些侮辱的始作俑者都是他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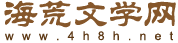
 连载中
连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