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仓库改为宿舍,其糟糕程度是难以忍受的。山里本来就冷,这仓库又高,空间又大,保暖性能极差,三月间夜里只有几度,被子带得薄了的人直说冷。冷还在其次,最难过的是人多。这一批来的新职工有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全部睡在这间仓库里,光是夜间打鼾的、磨牙的、说梦话的,就整夜的不清静。另外还有上厕所的,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没完没了,几次之后,那灯就长夜不熄地亮着了。有人睡觉浅,一有声音就醒;有人怕亮,说开了灯睡不着;有人从来没睡过双层床,说睡在上铺害怕会掉下来;有人干脆说不习惯和这么多人一起睡觉。
这话也算是大实话,谁和三百多人一起睡过觉啊。更兼男女一室,中间就隔着一道布帘子,两边人干点什么事,对面马上就听见了。上海的小姑娘们又娇气又细致,平时在家里就算像个小大姐什么都做,到了外面也是矜贵如大小姐。小大姐和大小姐虽说三个字完全一样,不过是次序颠倒一下,意思可是完全不一样。小大姐是帮佣,大小姐是小姐。小大姐可以和男的说笑打骂,大小姐是见了男的就别开眼。来的这些小姑娘,大部分是小大姐的出身,但不妨碍她们像大小姐一样的高傲。
三百多新职工里,男青年有二百多人,女青年还不到一百,男女比例是三比一,这让女青年们不像个大小姐也像个大小姐。《红楼梦》里凤姐说贾家的孩子,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在上海人眼里,也是一样的道理。没做过大小姐,但大小姐什么样子还是知道的。那么多旧上海的电影、良友画报、永安月刊、隔壁弄堂的沈家师母的姿势、自家姆妈讲的闲话、华山路上真正的大小姐的做派,无一不是上好的老师,把工人家庭出来的女孩儿潜影默化成了淑女。
说起来上海这个城市真是出产淑女的。淑女不是贵族,不是大小姐,淑女不讲出身门第,只讲自身的修养。在这个远离上海的安徽山区,每个人都像是重新出生了一次,光鲜干净得和其他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管是来自番瓜弄的棚户区,还是淮海路的上只角,全都抛开改变不了的过去,重新做人。
正因为如此,女孩儿们才清白水灵透着矜持劲儿地在山里做着大小姐的梦。有这么多男青年随她们挑呢。除了同来的二百多男青年人,还有不少老职工还是单身汉,在这个女性资源稀缺的地方,只有旷男,没有剩女。
有的男性,天生就会喜欢去讨好女性,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把每一次挫折当做动力,这边吃了瘪,那边回去就在男性面前吹嘘。小黑皮刘卫星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到达的第二天就对已经相熟的仇封建、徐长卿、还有睡他下铺的一个白净面皮的小白脸叫师哥舒的说:“申以澄是我的了,你们不许跟我抢。”
小白脸师哥舒问:“哪个申以澄?”
“喏,就是那个在看报纸的的,扎两根小辫子的那个。”刘卫星指给他看。“我已经问清楚,她叫申以澄,名字好听伐?老徐,昨天问你你还不答,你以为你不说,别人也不说吗?你以为你藏得住这么一个大美人吗?我只不过出来打个早饭,马上就搞清楚她的来历了。她父母都是虹口中学的老师,所以普通话说得这么标准。不过呢,父母都是臭老九,她也就摆不起架子了。这次会来小三线,就是和你们厂的红革委头头搞得不开心,人家看上她,她不同意,只好被发配沧州。”刘卫星问徐长卿,“你们一个厂的,你们那个红革委头头是不是这样的?听说是专门喜欢搞人家小姑娘?”
徐长卿抖一抖手里的光明日报,说:“批林批孔,斗私批修。我看斗私批修很好,私心杂念修正主义是该批。批林嘛就不用说了,孔老二可以批的地方多得很,‘克己复礼’倒也用不着批。克己复礼复的是周礼,批孔不过是批周,可是周公已经被批倒了。哎,你们看今天的头条,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又在批邓了。嗯。”仔细看报纸,对刘卫星品评美女一点不感兴趣。
刘卫星没趣,转而对仇封建说:“我看这里差不多一百个女的,就数申以澄顶好看。你这个篮球标兵长得也不错,你要是下手,我就争不过你了。我们说好,谁先看中就是谁的,是我先说的,你就不许再动脑筋了。”
仇封建看一眼申以澄,瞪着刘卫星说:“她要是找我呢?”
刘卫星不屑地说:“她为什么会找你?”
“你说的,篮球标兵嘛,也许人家喜欢运动员?”仇封建反问他。
“人家连红革委头头都看不上眼,会看中你?”刘卫星不服气。
仇封建说:“我是说万一。万一呢?”
刘卫星无耻地笑着说:“没有万一。老子先下手为强。还有你,小白脸,”他又找师哥舒的碴,“你别以为你是小白脸就可以占我便宜。”
小白脸哼一声,“要占便宜我也不会占你的便宜。”细细地观察了一番申以澄,嗤之以鼻地说:“再好看也不过是个女人,再好看,哈,再好看,拉屎也一样的臭。”
这话说得四个人都笑了。上头做报告的方书记听见了,放下红头文件大声说:“安静,不要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厂委传达中央重要文件,不但要认真听,还要认真做笔记。”拿起文件继续宣讲。
这是新职工的集中学习班,凡是新进厂的小青年,都要先学习,考核达标了,才能分到下面的小组去,由老师傅带徒弟地带着进行工作。学习班有长有短,徐长卿刚进机床厂的时候,学习班是两个星期,后来分到齿轮车间的翻砂组去,搬了一个月的生铁毛坯,两双劳动布工作手套重叠戴着,一双也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再把新的套进旧的里面,多的时候套四双,一双手才算保护下来了。
凡新工人进厂,总是要被老工人收两天骨头的,就看这一个月表现好不好,听话的乖巧的能干的聪明的分到好的岗位,笨的懒的不亮相的,分到吃苦受累岗位津贴少的工种去。徐长卿是上海人说的敲敲头顶,脚底板会得响的那种聪明人,这一个月咬咬挺了过来,老师傅看在眼里,知道这是一个学得进的好苗子,分工种时特别照顾,分配到了检验组。检验组是所有工种里最轻巧最省力最花眼睛最考头脑的一个岗位,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同时进厂的一批青工,进检验组的不过三个人。其中一人就是申以澄。后来申以澄因为一口普通话被人看中,抽调到了工会,是以徐长卿和她真的不熟。
这次学习班一开就是一个月,天天传达上级中央的最高指示,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批完孔又批林,批完林又批邓,评完水浒评红楼,白天听课,晚上还要写思想总结汇报。
徐长卿宁愿评水浒评红楼,这总要比批林批孔有意思。只因为毛泽东说宋江是投降派,于是全国就评上了水浒,新华书店一夜之间书架上全是水浒。又有一天毛泽东又说红楼梦第五回写的“护官符”是全书的大纲,是反动统治阶级互相勾结鱼肉百姓的工具,于是全国又开始评红楼。徐长卿内心是很感激伟大领袖的,若不是他忽然看了水浒评水浒,看了红楼评红楼,他从哪里去找古典小说来看?家里原来有的,都被他那胆小的母亲烧掉了。就算不烧掉,也不能光明正大地看,义正辞严地评。
小黑皮刘卫星本来不喜欢徐长卿,觉得他清高,但批林批孔批邓公,评完水浒评红楼,要交的思想总结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有时想出了点自以为很高明的见解,一旦要落在纸上,就又犯了难。十个字里面,倒有三个字不会写。
他拿了笔就骂:“册那!老子小学学军,中学学农,就没有学过文化课,现在倒又叫老子写古文。古文,它认得老子,老子不认得它。老徐,帮忙写一篇?”
徐长卿哪里肯帮他写,但经不住他软磨硬泡,不停地在耳边聒噪,只得写一篇让他交差,好让耳根子清静。刘卫星因为要求着他写批判稿,不得已,只好和他维持着表面的友谊。有谁愿意老是求人呢。因此两个人对这个学习班都是心里巴不得早点结束,一个是不想去求不得不求的人,一个是不想去理睬不得不理睬的人,表面和和气气,背地里厌之又厌,都在骂这个该死的学习班怎么还不完。
对于新职工仓库宿舍里彻夜不灭的长明灯,厂方头痛不已。先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要节约闹革命,十多个一百支光的白炽灯,一晚上下来要浪费多少电?你们算过这笔帐没有?
新职工说,我们来之前,你们是怎么许的愿?你们不是说“靠近黄山,风景幽雅,条件优越,设施齐备”吗?这难道就是“条件优越设施齐备”?至于“靠近黄山”,天知道这个山沟靠近哪一座山?靠近北京的金山也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天天上学习班,黄山啥个样子,没亲眼见过,阿拉是不晓得的。你们当初许的愿没有一条兑现,让我们这么多人男男女女住一间房,夜里不开灯,万一摸错了床铺怎么办?
说这样怪话的自然是刘卫星。他牢骚最多,怪话也最多,又敢说又敢做,仗着根正苗红,厂领导革委会武保队统统不放在眼里。又爱出风头,掼派头,引得女青工来看他,引得她们吃吃笑,就高兴得忘乎所以,越加的肆无忌惮。
童队长听得火冒三丈,骂道:“小赤佬①,不要为流氓行为找借口。这么多人,为什么别人不摸错,就你摸错?要不是故意的,先找什么借口?你要是敢半夜摸错床,老子第一个办你的学习班,先治你一个流氓罪,一点都不冤枉。”
刘卫星哪里怕他,也跟着拍台拍凳,冷笑道:“谁流氓?谁流氓?我家三代工人,阿爷是包身工,住的滚地龙,爷老头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闸北电厂的司炉工,全天下都是流氓也轮不到我流氓。你敢污蔑无产阶级,我看你才是拿摩温②,仗着你的红袖章,东摸西搞,那天就看你摸人起老阿姨的屁股了,你不是流氓谁流氓?”
“啊呸!”童队长恼羞成怒,瞪着眼睛训斥:“你敢造谣生事诽谤老职工,我看你是想蹲学习班了?”
“别拿学习班吓唬人,老子天天在上学习班。学习怕啥?我从幼儿园起就学习了,学到现在,屁股都学出了老茧,要不你也摸一摸?”刘卫星抄起胳膊斜着肩膀抖着腿问。
童队长说不过他,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刘卫星为他取得的第一回合胜利大肆宣扬,对女青工们吹嘘说:“不要怕他,将来他要是敢摸你们,来告诉我,我去整他。”
女青工本来把他当英雄,觉得他为大家出头,很了不起,听了这话,又啐了一声,一哄而散了。
刘卫星神抖抖地回来跟仇封建徐长卿师哥舒说:“看到没有?她们崇拜我。”
师哥舒带着怀疑地神情问他,“你说你三代工人,怎么也会被分到这里来?”
仇封建也好奇,捅一捅他,叫他快说。
刘卫星唉声叹气地道:“轮到了呗,谁敢不来?你们也都晓得的,市里的精神,分配工作是有顺序的。老大是市工,老二就是市农,老三是外工,老四最倒霉,只能是外农了。我大姐进了我爷老头子的闸北电厂做了工人,我二哥就只好去崇明的农场修理地球。轮到我,只能是外工,就来了这里。我还有个小弟弟,过两年挨到他,只好去江西落集体户了。你们呢?”问仇封建,“按道理说,你一个打篮球的,应该能留下来不走的?”
仇封建摇头说:“篮球队解散了。自从周公死后,厂领导怕大家聚在一起会有反革命的言论,那以后所有工会活动就都取消了。我比赛打得太多,工作做得太少,车间主任本来就不满意,车间里别的人跟我又不熟,分配名额一下来,自然就挑中了我。这个就是伟大领袖说的福兮祸之倚矣。”仇封建虽然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书也没正经读过两天,但评了这么久的水浒红楼,古文还是会一些的。那个时候,人人还有一句古文背得溜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仇封建说完,自然就该徐长卿交底,但徐长卿却接下仇封建先头的话,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一死,天下大乱。清明节那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有几万青年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敬献花圈,听说当天就关了不少人,过了两天,就说评定为反革命事件。你们厂的头头高瞻远瞩,提早解散,保了你们一条命,你该谢谢他。”
仇封建听了吓一跳,问“你怎么知道的?”
师哥舒嘴快,抢着说:“他有一台十二管的半导体收音机,我看他一回宿舍就躲在蚊帐里收听,是消息灵通人士。”
刘卫星一听,眼睛发光,说:“哦哟,灵的嘛,你藏得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老帅,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借给你听过?”
师哥舒本来姓师,但随大流叫老刘老徐老仇什么的,就有点尴尬,明明他是这几个人里最小的,这么一叫,倒成“老师”。管个小孩子叫老师,没人愿意,他也不敢答应。若不叫“老”师,改叫“小”师,听上去总不像样。亏得刘卫星脑子活络,把“师”字去掉一小横,变成“帅”,“老帅,老帅”的,听上去像是下象棋,“老帅”“老将”,带了点玩笑的意思,大家都没了意见。
老帅师哥舒说:“他才不肯。是他在收听敌台时我看见了。”师哥舒的床紧靠着徐长卿的,两人头碰头,隔着两层纱布做的蚊帐,影影绰绰的,那边做什么,这边还是看得见。
刘卫星看看学习班要结束了,可以不求着徐长卿,本打算以后不跟他要好,这一知道他有一台十二管的收音机,那还得了,马上谄媚相向,要借来听一听。又问:“可以听美国之音吗?”
徐长卿知道除非不要跟大家做朋友,不然,这件宝贝总是要给人分享的,虽然不愿意和刘卫星太过亲密,但人家求到面前,磨不开情面,还是要借出去的。何况这一个月写报告交报告也交流出些情谊,只好答应借他听听。
刘卫星捧了收音机,躲进蚊帐里调频调辐中波长波忙个不停,忽然掀开帐门对徐长卿说:“乖乖龙的咚,还有莫斯科电台!你小子瞒得这么牢。”放下帐门,又贴着耳朵听去了,羡慕得仇封建和师哥舒也挤了进去,一齐听那个美妙的女声说: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广播时间。接着音乐声响起,“索索哆西拉西哆来哆索”,歌词是大家都会唱的有苏联第二国歌之称的《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宽广》。听得三个人激动不已,又是捶床又是跳,不亦乐乎。
晚上吃了饭,几个人又躲在蚊帐里收听敌台,徐长卿在写毛笔字,拿了一张旧报纸写颜鲁公的《麻姑仙坛记》,这是他从家里带来的字帖。在这间巨大的宿舍里的工人,除了徐长卿,也有临帖的。有人临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有人临诸遂良《圣教序》,有人临柳公权《玄秘塔》,有人临王曦之《兰亭集序》,当然也有人临魏碑体的《雷锋日记》。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一切四旧都被打倒,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也在其中。但因为要写大字报,就必须要练毛笔字,而练毛笔字,就非要字帖不可。仕女图山水画都会被当四旧而烧掉,独独名家大师的字帖大行其道。王曦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麻姑坛圣教序玄秘塔,无一不是四旧,无一不是毒草,但没有人会对这些说三道四。在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练字临帖成了最好的消遣和最佳的学习方式,有心的人自然会从字帖中学到有益的知识,无心的人就算是临帖练字,也只是描红而已,帖里写的内容,并不是他会去关注和理解的。
宿舍里的人各干各的,一声“嗒的嗒”的喇叭声起,众人知道是九点钟了,休息时间到了,但也没人理会。这间厂是兵工厂,生产的是炮弹引信,作息也就按着部队的军事化管理方式,每天早上吹起床号,到了晚上吹熄灯号。但毕竟不是部队,吹了熄灯号不熄灯的多的是,大家都把熄灯号看成是闹钟,一吹号就表示九点钟到了,可以洗洗睡了。
这天熄灯号如期吹响,众人也没把它当回事,继续聊天的聊天,练字的练字,女青工有织毛衣的,看书写信的,也有人拿了盆去洗衣裳刷牙洗脸的,然后灯一暗,众人一惊,都呆在原地不动了。
有人大叫一声,说苏修打过来了。众人先是一愣,又都哄堂大笑,接着便有人说美国发原子弹了,台湾发地对地了。笑骂一回,等着来电。等来等去电也不亮,就有人坐不住了,说是怎么回事?跳闸了?保险丝烧断了?你们是不是有人在用电炉了?正嚷嚷乱成一团,有人打了手电筒进来,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队人,个个手里一只长手电筒,晃来晃去的晃得人眼睛花。
青工们先是一愣,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纷纷从枕头底下摸出自己的手电筒,也朝来人晃去。
打头的正是童队长,他拿着手电筒说:“鉴于你们新来的职工不遵守厂里的安全条例,整夜开灯,浪费电力,厂里经研究后做出决定,每晚九点钟吹过熄灯号后拉闸限电。”说完得意地笑笑,带了武保队的人扬长而去,把新职工们气得跳脚,却又无法可施。
大家骂了一通两通三通,乃至七通八通后,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这个现实。好在大家都带了蜡烛,在手电筒的帮助下,蜡烛从箱子里找出来点上了,该洗的洗该睡的睡,各自认命。
有人在烛光里骂:条件优越,设施齐备?骗人的鬼话。原来当初各厂的领导都是这么鼓动青工的。
又有人说,这算啥啦?当初歌里不是还唱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哈密瓜甜又香,骗了多少知青过去开荒?我们这里,总比新疆建设兵团要好一些。
有人附合说是,有人骂说阿Q。渐渐地也睡着了。
山里的夜异常的宁静,一片沉息里,可以听到屋后的松涛声和溪流声,衬得夜更静人更寂。不知是谁的一支蜡烛没有吹熄,又随着主人的翻身侧倒在床,“篷”的一声,蚊帐烧了起来,有人没有睡着,见了这黑暗里的火光,惊惶大呼,把大家都吵醒,又是忙忙的打手电筒点蜡烛,起火的蚊帐里的女青工被吓得在火光里大哭,旁边的人忙把洗过脸的湿毛巾都压在她床上灭火。
纱布帐子一烧即着,烧过就完,还没等火势蔓延到别的床铺,火已经被救灭了,那女青工整个身体裹在被子里,躲过一劫,众人把她从被子里捞出来,看她已经吓得脸青眼直,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姑娘吓得不轻,当夜就住进了后方基地的配套医院。新职工本来就有诸多不满,这下更是借机闹了起来,要宿舍、要电灯、要看电影,要有文体活动,就是没人说要工作岗位要上班的。学习班成了请愿团,新职工们围着厂领导七嘴八舌,反映情况。厂领导被吵得头痛,说回去和领导班子开个会,一定会商议个结果出来。
新职工老实了两天,坐等厂方的结论。到第三天,结论来了,在学习班上通告大家。
(一)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各人对政策吃得比较透,思想报告也比较深刻,战果喜人,准予结业。
(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节约闹革命,这是不会变的。晚上的照明灯准时在九点吹响熄灯号时拉闸,各人火烛小心。
(三)由于新宿舍楼不能及时盖好,因为造成新职工临时住在仓库里,对于因此而造成的不便,厂方深表歉意。经厂领导仔细研究,兹做出决定,把原来分配给老职工结婚用的楼房先让出来,让新职工们居住。
(四)学习班结束,新宿舍楼待建,修建队人员不够,特借调新职工去宿舍楼建筑工地,一应工作,听从修建队调配。
新职工们听了这四条决定,一时不知是该拍案而起的好,还是该欢欣鼓舞的好。不上学习班固然不错,可是要去修建队那里当小工,也绝对不是件高兴得起来的事。不住大仓库固然很好,可是也就没了与女青工们借抢水龙头的机会磨嘴皮子打情骂俏的乐趣。后来想了一想,大仓库总是要告别的,学习班也总是要结束的,熄不熄灯的,反正山里也没有更多的娱乐,到九点钟也差不多该睡了,这三条都没什么好争的,唯一一个就是去修建队报道,这个可是大大的不妙。他们是来当工人的,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修理地球的,想通这一层,马上高风亮节起来。
有人就说,我们是工人,我们进的是兵工厂,学的是保密条例,我们应该下到车间,站在机床旁边,造炮弹造引信,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修房子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下基层,与老工人们并肩作战。
厂领导说,既然大家认识都这么高,好得很嘛,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在哪里不是添?就在建筑工地上先干起来嘛,这才是真正的添砖加瓦。你们要和老同志并肩作战的想法也是很好的,老职工们在这里开疆拓土,住的还是没有煤卫的旧宿舍,但他们为你们如今的生活打好了基础,作为报答,你们就为他们添砖加瓦了。万丈高楼从地起,地基是他们的打的,砖是你们加的,大家同心协力,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你们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已经贡献给了厂里,贡献给了三线,贡献给了这里的大山,现在,轮到你们来把火红的青春献给伟大的社会。……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三线建设一天没有建设好,我就一天也睡不着觉。毛主席这么关心我们三线,我们怎么能辜负他老人家的深切厚望?难道你们忍心让他老人家这么大年龄还夜不能寐,为了三线建设劳心熬夜?苏修美帝在虎视耽耽,台湾人民还生活中水深火热之中,他老人家为国为民,中南海的灯光彻夜不熄……只要三线建设好,就算是原子弹也不能把我们吓倒。时代的巨轮即将起锚,共和国忘不了你们,人民忘不了你们……
他那里煽情滚滚,不知是谁在下面接了一句:“我们的妈妈也忘不了我们。”
马上有人接下去用佯装的洋泾浜苏北话怪里怪气地说道:“喔哟,我的妈妈呀,你的儿子在受苦哩。”这人的声音虽然伪装了,但一听可听出是属于刘卫星的。
本来这通气会开得气氛沉闷,厂领导的煽情只会引发更好的抵触情绪,老生常谈早就听得厌了。台湾人民水不水深火不火热管他们屁事,他们才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本来就有被骗的感觉,这些话听来竟是十分的反讽,厂部和新职工之间大有一触即发的战争,厂领导正愁怎么安抚这一批不安分的新职工,忽然被刘卫星这么一搅和,下面顿时笑声一片,笑倒不少的女青工,而厂领导则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刘卫星看见女青工们笑得东倒西歪的,越发的轻狂起来,不用苏北话说滑稽戏,改唱苏联歌曲了:“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翻来复去唱同一句,只为了这一句歌词里既有“亲爱的”,又有“吻”,这在所有他们会唱的歌曲中,是绝无仅有的。只是为了这两个词,他们可以把这首歌唱上一百遍。并且是对着心仪的姑娘,或是美貌的女青工,好象对着谁在唱,就是在叫谁是他的“亲爱的”,就是在“吻”谁了。
男青工把这首歌当情歌在唱,亲啦吻的,这种字眼从舌头上滚过,可是过足了嘴瘾。这样一来,女青工一听这歌,就条件反射地骂“下作坯”。这首歌曲也跟苏修一样,成了反动派。可是越反动的东西越是招人爱,男青年几乎要把这首歌当语录来膜拜了。
这时也一样,女青工一听便要开口骂,厂领导刚要训斥,师哥舒就说话了,同样也是用阴阳怪气的语调说:“朋友,侬妈妈把侬卖掉了。”师哥舒挺看不上刘卫星的聒不知耻,又和徐长卿私下交流过了刘卫星耍宝错失了和厂方对抗的机会,便开口讽刺他。
刘卫星反正脸皮厚,师哥舒的讽刺也没听出来,反倒借了他的话头,继续用苏北话说:“我的妈妈呀,侬哪能好把我卖掉呢?这是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啊。”他一扮小丑耍宝,又引得女青工们发笑。
厂领导求之不得,顺着轻松的气氛布置了任务,又宣布提前解散下班,回去搬行李换宿舍,厂里已经把所有人员排了名单,女职工一幢楼,男职工一幢楼。一间房间四张床,八个人,名单在这里,大家照着这个去搬自己睡的床。好了,解散。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笑眯眯地让新职工对着名单吵吵嚷嚷。
领导来了个金蝉脱壳胜利战退,留下一张排名表二桃杀三士,引开了注意力。要说老奸巨滑,这些才脱了娃娃气的新职工,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新职工忘了同仇敌忾要与厂方斗争到底,那九点钟的熄灯令,那下基建去挖烂泥全都不论,只是挑三拣四。有人嫌楼层不好,有人嫌朝向不佳,有人嫌同室倒不来,又有说我要和张三李四一间屋。边吵边回仓库,先拿了自己的行李箱子铺盖卷到宿舍楼,占房间要紧。吵完了又骂,骂完了又抄家伙,几乎要打起来,被冷静的人劝住了,平心静气后,又七手八脚地抬铁架子床。直忙到夜里,熄灯号吹响,这一天才算过完。
宿舍的住宿分配,终究还是打乱了领导的安排,各自选了脾气相投的人住进一间房。徐长卿仇封建刘卫星师哥舒几个,不知怎么又做了室友,另外还加了别的四个人进来,后来换来换去,又走了两个,便是六个人住一间房。
领导说话,从来说一不二,隔天就命令新职工们去基建工地挖泥挑土搬石头平整地基。开始没有人愿意去干,一个个在地里磨洋工。可是干了两天,却发现比坐在室内上学习班有趣多了。学习班要听报告写总结,听得昏昏欲睡,写得思想颓废,坐得屁股生疮,闷得魂游天堂。哪里比得上挖土担泥这么自由自在?
前面说过,这里是两座山谷底下当中的狭长地带,要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去一部分山体,用挖出的石头垒起挡泥护坡,以阻止一旦雨季来到,泥土会随着雨水流下来,造成山体滑坡。垒好护坡墙后,再平整地基,打地桩,浇地平,然后才砌墙。砌墙这样的精细活自然用不着他们来做,那是修建队的泥工做的,他们只需要做前面的工作:在山体上凿洞,埋炸药,拉引线,炸山。挖土,挑泥,搬石头。
兵工厂有的是炸药雷管和引线,开起山来分外的容易,半天半天的等着埋管拖线,大把的时间让新职工们消磨。这样的野外作业是很能激发起年轻人的热情的,他们会把炸石开山当成战争片,一样的硝烟弥漫,一样的石屑粉飞,他们几乎以为他们是在冲锋陷阵。他们不但唱“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这样的战争歌曲,他们也唱他们编写的小调。
那时有许多的小调流传在青年中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他们的歌曲,老三届人才济济,出了不少才子。他们以后的学弟学妹没有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求学时代,就像刘卫星说的,小学学军,中学学农,七0届以后的学生,虽说也是中学毕业,学识却等于小学生。老三届创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文斗武斗最后上山下乡,怎么也算得上是造出过声势做出过成就。而七0届以后则偃旗息鼓,什么都没他们的份,在上海被定为“无去向培训”的一批,几乎等同于三等公民。正经职工看不起他们,他们也感觉到了社会抛给他们的白眼,许多人便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离开了上海,加入了三线建设之中。
他们中间的小才子为他们写了歌,这样的歌词一经谱上曲,就在他们中间传唱开去。
“告别了黄浦江,告别了爹和娘。
兄弟们,不用悲伤,
姐妹们,毋庸思量。
我们远走高飞浪迹天涯,
我们闯荡江湖四海为家。
这里有条通向故乡的小路,
这里也有家乡一样的月亮。
别了亲人,
别了故乡。”
唱着这样的歌曲,矛盾在劳动中泯于一笑,在歌声中想念他们共同的家乡。
这时是四月中旬,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山里的野花开得漫山遍野,桃杏争艳,杜鹃红遍。这些还只是大家粗识的叫得出名字的,那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山花野花,一丛丛一串串,从山脚直开到山顶。
天气不冷不热的,干点小活,微微见汗,男青年脱了中山装,女青年脱了春秋衫,男青年比的是肩宽腰挺,女青年则是绒线衫勾勒出曼妙腰身。眼风一个个丢过去,笑话一个个说起来。土地没平整出多少,情侣凑足了几对。
刘卫星整天围着申以澄献殷勤。他这么一盆火似的,别的男青年自然不好意思再上来表示有意,所谓的好女就怕癞汉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癞汉霸占了好女的周围空间,还有什么好男会上去自讨没趣?美人的脸再好看,也比不上情敌恶狠狠的眼神和不时挥舞的拳头。
注①赤佬:方言,鬼,带贬义。
注②拿摩温:旧上海工厂的工头。是NO.1的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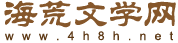
 已完结
已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