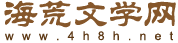《噬骨谋情:妻控待定》 第十章 我要杀了那个畜生 在线阅读
她妈是在去求陈均那天被撞死的,死得很痛苦,被碾成两半,过了很久才断气。
许慕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听完这些话的,她边哭边捶着拘留所的铁栏杆。
她出不去,她连她妈最后一眼都看不了。
她还记得宋庆珂醒来时,抱着她含糊不清的说,“不怪你。我的女儿,我相信...离婚就离婚,有妈妈在,我永远站在你这边,那群人,一定会有报应的,小宜乖,别哭!”
陈均,陈均,陈均....
她疯了般嘶喊这个名字,原来他压根不会得到报应!她为什么没杀了他,她早该杀了他啊!
有人抱住她,死死摁住她的肩膀,不让她动弹,许慕宜抬起头,终于看到傅斯年那双又沉又暗的眸子。
她失声痛哭,“傅斯年,帮我,求求你,帮帮我!我要杀了他,要杀了那个混账!”
傅斯年没有说话,许慕宜骂,“不是你要帮我吗?我后悔了,我知道错了,我答应你,答应你!为什么你不说话了,为什么啊?”
傅斯年抱起她,任由她疯了般捶打自己的胸膛,很疼,该疼!
拘留所外面,黎致远和袁一鸣站在门口,见傅斯年抱着人出来了,黎致远走过去,直接给许慕宜打了两针镇定剂。
几人就要离开。
苏觅一直跟着,见状奔过去,拦在车门前,“你们想带小宜去哪里?”
黎致远扫她一眼,“我是医生,他....”
他瞥了面色如冰的傅斯年一眼,轻声道,“是她男人。”
苏觅怔了怔,眼泪唰的落下,她扑过去,对着傅斯年大声质问道,“那你早干嘛去了?为什么等到这时候才来,这时候才来救她!你可是傅斯年啊,你怎么能任由这种事发生?”
她是真的怒到极点,忘了这人是她最敬佩,最想套近乎的男人。
她这些天,为了见许慕宜一面,找了无数关系,不为别的,只因为她知道,许慕宜是被冤枉的,她就是最好的人证啊,可没人相信她,就连报社也不信。
苏觅找到宋庆珂,才知道许慕宜真正的遭遇,苏觅简直不敢相信,她当时是忍着怎么样的心情,才能那么平静的说出离婚的事。
苏觅也恨,她自诩追求正义和真实的报道社会不平,可最不平的事就发生在她曾经最后的朋友身上,她却无能无力。
她家那么一点关系,她自己那么一点实力,在陈均,不,陈家面前,不堪一提。
可傅斯年是谁?
苏觅流着泪,不停的骂着,有自始至终,傅斯年一句话也没说。
袁一鸣受不了,下车把她往后拉,黎致远一踩油门,便扬长而去。
苏觅气得要追,袁一鸣将她扔进一辆警车,怒道:“你以为老大心里就好受了?他没来是因为他去救许慕宜她妈去了。他也被车撞了,肋骨断了好几根,可他找谁说,找谁骂去?”
苏觅一愣,袁一鸣气得青筋暴起,“你以为你怎么进来的,还不是老大疏通关系!老大想着你是许慕宜最好的朋友,能帮忙安慰她,你倒好,一股脑不管不顾什么也说了,你是痛快了,可她呢?她能这么刺激吗?”
袁一鸣是个温吞性子,就算骂人,也不是满口脏话,大声囔囔。
苏觅看着他,咬住牙,眼泪不停流,可到底没再骂人了。
她只望着许慕宜离开的方向,哽咽道,“小宜可怎么办啊....”
袁一鸣没有说话,他也不知道,大概这世上,没人能回答得了这个问题。
送宋庆珂下葬那天,下了场暴雨,声势浩大,有洗去一切痕迹的阵势。
许慕宜跪在墓前很久也没起身,傅斯年就站在她身后,静默的陪着她,两人都没有撑伞。
不知过了多久,傅斯年沉沉开了口。
他说,“许慕宜,跟我回家。”
家?母亲死了,她哪来的家?
父母在尚知来处,父母亡只知归途!
许慕宜没有抬头,她只问道,“傅斯年,你喜欢我吗?”
傅斯年沉默,她却笑了,“如果不喜欢我,就别招惹我。我是个扫把星,逮谁克谁。”
她顿了顿,指着宋庆珂笑得温和的那张遗像,“瞧,连我妈都被我克死了。”
话音刚落,傅斯年的手轻轻摁住她的肩,力道很大,摁得她肩生疼。
“我命硬,不怕克,不信你就跟我过日子试一试!”
男人的声音不大,却有种莫名的坚定。
许慕宜的眼泪顺着雨滴落下,她摇头,只不停的摇头。
她心底明白自己是不配的,这个男人有万般好,她哪里配得上?
两人之间纠葛那么深,只该有恨,有怨,偏偏她又生了感激,生了心动。
她知道这个男人不爱她,不喜欢她,也许只有那么一点歉意,便无端生了如此多的纠缠。
傅斯年抱住她,语调很硬,声音急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许慕宜,我不会让你跟着陈均同归于尽,他不够格!要报仇可以,可你更要好好生活,这样阿姨泉下有知,才不会为你担心!”
听到他听到母亲,许慕宜一颗心疼得几乎要被搅碎。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傅斯年,你之前为什么想杀陈均?难道不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吗?”
“正是因为我做过,所以知道不值!”傅斯年手上力气加深,他眉目明明英俊无比,却透着种说不出的桀骜冷酷:“给我好好活着,这样才能干你想干的事。报仇?不是杀了他,要让他生不如死,把他狠狠踩在脚底,让他永远恐惧你的存在,求死而不得才对。”
许慕宜没说话,傅斯年便执拗的抱紧她,像要把她嵌进骨子里似的,两人亲密无间的贴在一起,没有爱意涌动,却暗潮汹涌。
后来,许慕宜还是跟着傅斯年回了那城堡一般的地方。
乐姨不在,那个傅斯年对她格外温柔的女人也不在。
偌大的屋子只有他们两个人。
傅斯年给她熬了粥,喂她吃过,又抱着她去了浴室。
热气霪然的浴室,傅斯年平静的剐了许慕宜的衣服,将她放进浴缸,又打开莲蓬头给她洗头。
他动作有些生硬,眉头蹙着,很专注的样子。
许慕宜缩在浴缸,看着他。
很奇怪,明明待在最暧昧的空间,做着无比亲昵的事,两人却都很坦然。
甚至,傅斯年还轻轻拂过她腹部的伤疤,那是一道很深很渗人的伤疤,直到此刻,傅斯年才知道乐婶说的,“那孩子一身伤,看着怪可怜”是什么意思。
他竟有些颤栗,手似碰,又不敢碰。
许慕宜似乎懂他的颤栗,伸手握住他,然后轻轻滑过,“傅斯年,你不欠我的。这里,该陈均还!”
傅斯年深吸一口气,抱住她,有种虔诚的味道。
他微微弯下shen子,冰冷的唇轻轻吻了下那道疤,许慕宜觉得自己有些发抖,可她没有躲闪,就看着男人保持这个姿势,待了许久。
后来,傅斯年直起身,给她穿上浴袍,又给她吹干头发。
两个人就这么躺在一张床上,犹如恋人般相拥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