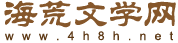《银河街十日谈》 楔子 在线阅读
『初夏去银河街听老故事,是我今年做过最浪漫的事。』
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看:茂密的梧桐树叶将天上的大日头遮得严严实实,只剩稀疏斑驳的光影倒映在街道上。对面一排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皆被护在这壮实的树干下,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平和而宁静。
这是农历的五月初,南江将热未热。但中午十一点,却已很有一些夏日的气氛。
一慧挂了电话,过来拉我:“走,吃饭去。”
我懒洋洋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同她踩着木质的梯子下了楼。
屋前的人行道有些狭窄,仅能容两个人并肩通过,再往外就是树了。街道倒是四车道,只是也逼仄得很,仿佛平行的两辆车随时会擦到对方反光镜。我跟着一慧走了几步,瞧见路牌上写着“银河街”三个字,便忍不住揶揄:“银河街?就这种宽度吗?”
“你是不晓得。”一慧说,“这街民国时就有了,树、房子,全都是那时传下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说要拆迁,还是一个华侨建筑师力争留下的。只是路太窄,前几年把树往里挪了几公尺,才勉强辟出四车道来。”
她边说边带我拐进屋后的小巷子去取车,刚要拐进弄堂时遇上一个六十来岁的中年妇女,衣着不算多考究,但气质倒是少见的平和。一慧见了她便招呼道:“谭阿姨,巧呀。又来打扫卫生?不是半个月一趟么,你上个礼拜刚刚来过呀。”
谭阿姨立定了笑:“齐老先生今朝就要回来了,我先来通一通风……哎哟!话曹操曹操就到了喏。”她小跑了两步迎上去。
我和一慧回过头去看,瞧见一辆沃尔沃SUV停在路边,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从驾驶室下来,绕过车尾,拉开副驾后面的车门。那是个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身形挺拔,白肤鹤发,穿着西裤配衬衫,外罩一件马甲,挺括得老远一看就知是顶级的质料与手工。
那年轻男子拉了车门边要伸手去扶,老先生早已迈步下了车,一手撑住精细的手杖,一手轻轻往下压了压:“吾可以咯。”是一口标准的上海腔。
谭阿姨急了:“齐叔,吾鞭炮还没放了呀!侬哪能先下来了。”
老先生笑:“阿梅,啥年代了,好省么省了呀。现在不是人人关心PM2.5了么。”
“哎哟。”我听到此处侧头悄声同一慧讲,“这位老先生看起来像是个有钱的知识分子啊,派头太足了。”
一慧瞄我一眼:“还‘像是’呢,摆明了就是啊!”她拉我,“走吧!午饭还吃不吃了,我都快饿扁了。”
两人吃过午饭又就近找了家咖啡店。
一慧问我:“接下来呢,你打算怎么办?”
我据实以告:“能怎么办,又不是家财万贯,总归休息个把月,回去再找个工作。”我新近辞了工,一慧知晓后立即打电话给我,叫我来散几日心,我也就不客气,乘了半小时高铁来这里。
“小说呢,还写不写?”
“当然要写,人生理想嘛。”
她笑起来:“那就好。”
杯中美式饮尽的时候,两个人站起来,照旧驾车回银河路。一慧开了家软装工作室,客户多是预约上门,因此有空在午后陪我三个钟头。
我坐在副驾上,不必再忧心街道宽窄,只觉得银河街真是出奇的美。道路两旁的梧桐树长成拱形,包裹住整条街道,往前望去,一片碧绿好似没有尽头。路的两旁开着形形色色的小店,无一不雅致安静,这个点,行人不多,麻雀闲散地站在枝头叽叽喳喳,小猫咪慵懒地躺在石板路上。我忍不住感叹:“一慧你真是会挑地方。”
“那当然。”她说着将车拐进小巷口,又把我先放下来,“里面位置窄,不能从车门出来。”
“那你呢?”
她指了指天窗。
我笑得直不起腰:“你真是一如既往好身手啊!”
在巷子口等一慧,仍然是遇见谭阿姨的那个地方。
此刻这里停了两辆面包车,两个工装服的中年人正把一个个纸箱搬进屋子里。我百无聊赖,便站着看。孰料“哗啦”一声,那纸箱底裂开,里面的书籍散了一地。
搬箱人“哎哟”一声,屋里即刻冲出来一个年轻男人,正是上午见过的那辆SUV的车主。他扫了一眼地上的场景,当即捂脸吸了口冷气,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蹲下来就捡。搬货人见状也七手八脚就抓。
“轻点。”年轻男人开了口,声音圆润平和,朝气十足,倒是与长相成正比。
地上散着一堆书,远望似乎还是古籍,微风一吹,纸页哗哗作响,我心疼得紧,看不过眼只好凑上去一起捡。年轻男子愣了一下,随即朝我露出微笑:“谢谢。”
我合上手中书籍的封面,正要应声,低头却赫然看到手中是一册刻本《史姓韵编》品相一流,摆印精准,绝非当代仿本。我心下一惊,细细端详了两眼,忍不住夸:“好书啊!”
“是。”有人这样回答,音色苍老而沉稳,我抬起头来看,是中午被王阿姨唤作“齐叔”的那位老先生,他拄着拐杖向前走了两步,站直了笑,“小姑娘识货的,这版的《史姓韵编》可是内聚珍。”
他这样一讲,我手上不由愈加慎重,轻掸了灰尘,小心翼翼地码进箱子里,又一一去捡地上的书,都是古籍,《庄子集释》《文心雕龙》《胡子衡齐》不一而足。
将一本半旧的线装书从背面翻过来的时候,我难抑激动地“呀”一声:“汲古阁的《六十种曲》上百年前就几乎已经绝版了!”
“是。”老先生声音里有一点或者称得上欣慰的笑意。我抬头看他,在黄花梨手杖的支撑下,他脊背挺直,逆光而立,宛如一棵老松,顽强得足以刺破时光,似有无尽力量。
一慧从巷子里停了车出来,老远嚷嚷:“阿砚,干嘛呢?”
书已捡尽,我站起来,等她走近。
正要告辞,老先生忽然笑道:“小姑娘,要是不忙,进来吃杯茶好哇?我们怀信泡茶一流。”他换成普通话,仍略带一点沪语腔。
我和一慧正面面相觑,被叫作“怀信”的年轻男子已接过话头,捧着纸箱笑眯眯道:“两位请。”
推辞似乎已经不礼貌了,我们应一句“叨扰了”便转过屋角进了门。
屋子进深比开间要大一些,物件不多,但古色古香,左侧是一排高大的书架立在墙边,即便认不出木质,但看一眼色泽也知价值不菲。书桌圈椅摆在书架前,笔墨纸砚样样齐全,老式唱片机搁在博古架上。右侧是一张长约二米的茶桌,做旧的样式,看样子是新置的,桌上摆着整套的茶具,壶与杯都是紫砂质地。紧邻着的窗边摆着绿植,水仙开得正好,睡莲也枝繁叶茂。一张躺椅静静倚在窗下。
整洁得堪称一尘不染,但却并没有故意的陈设感,熨帖且自然,老先生进屋来悠悠地坐到茶桌前,那种放松欣慰的姿态仿佛一下子让整间屋子鲜活起来,那是深情的主人才能有的神情,客居者是培养不出来的。
他坐在太师椅上唤年轻男子:“怀信,你去里屋把第二格抽屉里那块普洱拿下来。”
男人应声进去,少顷拿一块茶饼出来,撕开纸,细细掰碎放进茶壶里。
谭阿姨戴着围裙从里屋出来,手上端着一个果盘,摆着红豆酥和杏仁饼,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别客气,多吃点。”
老先生坐在我对面:“小姑娘,现在像你这样懂古籍的不多了噢。”
“略知皮毛。我爷爷爱藏书,耳濡目染的。他找了半辈子刻本《史姓韵编》都没找到,所以我印象格外深刻。”
老先生笑道:“那回头你替我把这本带给他,宝剑赠英雄。”
我摆手:“不不,不敢夺您所爱,况且他老人家已经过世。”
“这样啊……”老先生像有点喟叹的样子,但神色如常,并不能瞧出情绪,“物是人非啊。”他忽然说,“眨眼雁宁也走了一年了。”
年轻男人替我们倒过茶,伸手轻拍老先生背:“阿爷……”安慰声轻轻,似哄孩子。
老先生倒笑起来了:“今朝刚回来,难免睹物思人。”
男人来了兴致:“阿爷,我老早听奶奶讲,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差点打起来?”
“伊个能讲个么?明明是伊差点打吾。”老先生讲起从前,眉眼都带了笑意。
“那您给我讲讲,我给您拨乱反正。”
“客人还在,讲老里八早的事体岂不是扫兴。”
“不不,您讲。”我和一慧异口同声,“再感兴趣没有。”
“既然这样……”老先生端起茶杯,抿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