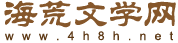《桃花》 第九章 仿佛依稀(9) 在线阅读
两个人坐了一会儿,新容叹了口气:“没有你我可怎么办?”
“没有我你什么都能办。”梁赞说,“我们刚到杂志社那会儿,我每次见你你都在干活儿,拼命三娘。”
新容笑笑,看看梁赞:“抱抱我吧。”
梁赞倾过身子把她抱在怀里,过了一会儿,笑了。
“你笑什么?”新容问。
“如果现在我让你跟我回家,你肯定会跟我走的,但那样一来我就成了小人了,不要说你,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不过,只怕过了今晚,也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了。”
新容没想到梁赞长得人高马大,倒长了一副玻璃肚肠水晶心肝,不过他把话挑破到这个程度,她反倒不能承认了:“谁要跟你回家了?别臭美了。”
“我又自作多情了?”梁赞自嘲。
“你也折腾得够呛,早点儿回家休息吧。”她拉开车门,“我走了。”
梁赞一句话不说,看着她。
“我走了?”新容又问。
“你再锇怂舻模绷涸扌πΓ拔揖筒蝗媚阕撸涯憷丶胰ァ!
新容这才下车,低头看着梁赞。
“好好洗个澡,睡一觉吧。”梁赞轻声说,一踩油门,车子蹿进了夜色。
葬礼前,新容拉黄励去了一趟“卓展”,一人买了一套黑色套装,照着自己的款式,给徐文静也挑了一套小号的。
“干吗花这个钱?”黄励一看价签就急了,“我结婚也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啊。”
“平时也能穿。”新容低声劝。
“正经寡妇是人家徐文静,我穿上算什么?”黄励嘟嘟囔囔的,衣服一穿上身,到底是名牌货,马上把人衬得有模有样儿,连气质都出来了,黄励又惊又喜地看了新容一眼。
“要不,我要套别的颜色,平时也能穿出去。”黄励跟新容商量。
“那我再给你买一套。”新容说。
“别别别,”黄励心疼钱,“就这么着吧。”
新容让售货员开票。
不光外衣,内衣、衬衫、鞋子、袜子,连抹眼泪用的手绢都每人买了三个备用,黄励心疼得直抽冷气。
买完衣服新容又把黄励拉进“紫梦”,专点那个收费最高的“大工” 阿坚给黄励设计新发型,“紫梦”在新容的杂志上做广告,算是关系单位,打了个六折还要七百多块钱。
黄励死活不肯,被新容硬摁在椅子上。新容也想顺便给自己h个油,大工刚过来,她就接到徐文静的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儿:“新容,你来一趟行吗?”
新容把黄励安顿好,拎着要给徐文静的东西去了酒店,刚敲了一下,徐文静就开了门,她憔悴得不行,黑眼圈儿像是让人打了两拳。
“我不敢睡觉,一闭眼睛就觉得苏老师在房间里四处溜达呢,还念诗。”徐文静可怜巴巴地说。
“境由心生。”新容说,“是你自己总想着这件事情闹的。”
“不是,”徐文静四下看看,“他真的在这儿。”
房间是普通的双人间,两层窗帘都挡着,屋里又闷又热,空气很坏,徐文静穿着衬衫牛仔裤坐在沙发上抱着自己膝盖还浑身哆嗦,确实有点儿邪门。
“他真在这儿的话,也不会伤害你的。”新容说,“听说,死去的人最惦记谁,对谁最放心不下才会守着他(她)。”
“他肯定在这儿。”徐文静哭出来了。
新容给梁赞打电话,说了这边的事儿。梁赞也想不出主意,说打听打听再给她们打电话,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打电话过来,嘱咐她们收拾收拾,二十分钟后他带她们去个地方。
“去哪儿?”见到梁赞,新容问。
“还是老聂给想出的办法,说有个袁先生,治这种事儿是大拿。”
袁先生七十多岁了,房间里面非常简陋,点着线香。袁先生目光如炬,从他们一进门就盯着徐文静看,梁赞刚说有位亲人过世,他就微笑着对徐文静说:“这位先生跟你关系不一般啊。”
徐文静脸色煞白,顺着袁先生的目光往自己左肩膀后面瞅。
袁先生念叨完一些徐文静听不懂的话,然后用红笔在黄纸上画了个符烧了,兑上点儿凉开水,盛水的杯子好像是二十几年前的搪瓷缸子,上面污迹斑斑,但徐文静还是把水喝了个精光。
“这样就行了,”袁先生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剩下的事儿全交给我吧。”
梁赞掏出五百块钱放在袁先生的桌子上,带她们走了。
第二天举行葬礼时,黄励、新容,还有徐文静换上新买的衣服,三个人往殡仪馆告别厅门口一站,既庄严,又美丽。
“你们太漂亮了。” 亦晴拿数码相机把她们三个拍了下来,凑过去给新容看,“爱与哀愁。”
“别瞎胡闹,”朱秀茹训她,“不看看是什么地方。”
花店送来预订的白玫瑰花,来参加葬礼的人每人拣一朵戴在胸前。杂志社的人一个不落,都来捧场。
苏启智单位来了两个工会干部,看见她们三个并肩站立迎宾,非常意外,接着便露出感动的表情,态度也变得积极了。黄励虽然退休了,也来了几个平时跟她处得好的姐妹,见了面先是吃惊,两三年没见过,黄励怎么越活越年轻,越来越精神,说了几句闲话又落到苏启智身上:“虽然他是自己招的,可你也真是命苦啊,现在又这样不计前嫌――”老姐老妹们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这辈子他欠你,下辈子他为你做牛做马。”有人安慰黄励。
徐文静没料到她的哥嫂竟然会来,拉着他们的手,眼泪像扭开的水龙头,她哥嫂看看卧在几千朵白玫瑰、白百合、白菊花中间的苏启智,叹了口气,眼圈儿也跟着红了。
“已经到了这一步,就节哀顺变吧!”
梁赞没怎么在人前转,但新容看他处处都在。来宾致哀时,他跟朱秀茹一起,很规矩地给苏启智鞠了三个躬。
所有来宾致哀完毕,主持人又说了几句套话,宣布葬礼结束,苏启智身下的折板一开,他坠入滑道,待她们三个反应过来,玻璃棺材里面已经空了。
“苏启智!!!”徐文静和黄励同时喊出来,接着哭声乍起,黄励的朋友拥过来扶她,新容抱住了徐文静,泪水泉涌而出。
午餐是梁赞安排的,他的一个朋友开了一间小型日本料理店,被他包了场。小店环境清雅,服务员穿着和服等在门口,大家排着队去卫生间洗手,半个小时才洗完,餐厅中央一个大长条桌上摆着食物,长桌的一边是日本清酒,另一边是各种饮料,周围散开六张六人位的桌子,黄励跟朋友一桌,徐文静跟她兄嫂一桌,新容陪苏启智单位的人坐,朱秀茹和梁赞也代表杂志社陪着他们,剩下都是杂志社的人四处散坐着。
大家都夸葬礼办得好,没见过这么高雅的。
“苏老师名士风骨,到底和俗人不同啊。”他们单位的人感慨。
吃完饭人一拨儿一拨儿地散了,最后只剩下新容和梁赞。跟老板结了账,道了谢,走出店来,外面阳光炙热,街面反射着白花花的阳光。
“去哪儿?”梁赞问新容。
新容一时不知何去何从,黄励带着她的朋友们回家去了,单位嘛,刚才朱秀茹跟她说这几天不用上班,一是家里还有不少琐事要处理,另外,也尽可能多陪陪妈妈。
“那我们就随便走,碰到什么算什么,”梁赞问,“怎么样?”
“好啊。”新容说。
梁赞只是开个玩笑,倒没想到她竟答应了,扭头看她一眼:“真的?”
“真的。”新容说,“遇仙成仙,遇魔成魔。”
他笑了,把车开上一条路,新容懒得往外看,懒得想梁赞要把她带到哪里去,更懒得猜测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眯着眼睛,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街景,想着那天在大连,那个下雨的午后,她跟苏启智坐在酒店咖啡吧里聊天,她喝着刚送来的卡布奇诺,而苏启智只能闻一闻他要的蓝山咖啡,不过,在深吸一口气后,他脸上的表情倒比很多喝咖啡的人更陶醉:“你知道有个叫路易斯・辛普森的诗人吗?”他问。
新容摇摇头。
苏启智说,这位诗人写过一首叫《美国诗歌》的诗,他之所以记住了这首诗,是因为诗里提到了胃。接着他给她读那首诗,用很慢的语调:
不论它是什么,都必须有
一个胃,能够消化
橡皮、煤、铀、月亮、诗。
就像鲨鱼,肚里盛只鞋子。
它必须游过茫茫的沙漠,
一路发出近似人声的吼叫――